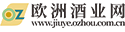*旧文重发,稍作修改
*已放入《马嘉祺》文集,上集可自行前往查看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*准备好纸巾,请耐心观看
你=余婉
也忘了是谁先开的口,后来你就常在马嘉祺家蹭饭。他会做黑椒小牛菲力、法式奶汁青口、草莓啵啵蛋糕,你吃了一个月白食,腰围以目力所及的趋势见涨。
你先前还不好意思,执意要出自己的那一份饭钱。
马嘉祺正吃着饭,淡淡一笑,一双骨节修长的手放下刀叉,将钱慢慢推了回来。
你只觉得马嘉祺身上有种不容置疑的定力,你只是看他的姿势、他的神态,就心知肚明他不可以用世俗的客气来衡量。
马嘉祺从不做中式菜,你只问了一次,那晚他正在厨房做意面,你注意到他的背僵了一僵。
“你知道人做饭是会带有印记的吗?”
“什么印记?”
他笑笑,没有回答。
四月一号那天碰上周末,你过来吃晚饭,发觉今天的菜都是海鲜,七七八八的碟子排了一桌,还开了一瓶白葡萄酒。
马嘉祺做饭是私厨的水准,酒又好喝,你吃得形象全无。
马嘉祺吃得倒少,一直望着你笑,问你好不好吃。
你拍着肚皮坐在餐桌前,只觉得再满足没有了,叹了口气道:“要是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死就好了。”
马嘉祺闻言站起身,他的家清简至极,一居室客厅里只放着一张白木餐桌、两把椅子。
他走过去熄了灯,你先是吃了一惊,继而安下心来。
在夜的黑里,一双手从身后轻轻揽住你的肩。
你被那双手带起身,在空旷的客厅里跳舞。起先你还笨笨地总是踩到他,后来就被他带得很好了。
这会儿你已经逐渐适应室内的幽暗,隔街喧嚷的市声,流溢的霓虹,路灯暗淡昏黄的光线一一从窗外透进来。
地板上印出田字格的窗户投影,你们踩在这阴影里,好像离世界很近,又好像和世界毫无关系。
男女之间暧昧未尽的静谧,每一刻钟都有着岁月绵长的温柔。
马嘉祺带着你在阴影里轻轻地旋转,没有灯光,没有音乐,马嘉祺身上有古龙的清香。你忽然眼睛潮湿起来,将头轻轻靠在马嘉祺的胸膛上。
马嘉祺忽然喃喃道:“有一年大雪天,清早我去个园,没有什么人迹。白雪覆在竹子上,清清白白,天阴阴的,还在落雪。
我仰头看,发现雪在空中看起来是黑的。你说,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吗?比如黑,和白。”
如同梦呓。
你闭着眼:“下次大雪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那个园。”
“好啊。”
“那么一言为定。”
朦胧中,你似乎觉得自己额头上落下一个湿润的吻。你醉得厉害,却很想睁开眼睛看看马嘉祺,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抱着自己在跳舞。
......
醒来时你已经在自家的床上,外套挂在衣帽架上,鞋子被擦得干干净净放在门后。
你身上覆着棉被,四月的阳光透进来,乍看之下有种疲倦的暖意。你心里一激灵,伸手拿过床头的闹钟,已经是下午三点。
你只觉头疼得厉害,起身去厨房倒水喝。久未启封的炉灶上放着小小的陶罐,揭开盖,是一罐普普通通的白粥。
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做的,你微微一笑。案板上一字排开三个小方碟,咸鸭蛋、萝卜丝、苦瓜干,朴素清简的食物在宿醉后有种熨贴人心的安慰感。
你用小碗盛了粥,捧在手心里慢慢地喝。温热的粥水下肚的瞬间,你像是想起了什么,马嘉祺做的是中式早餐的廉江白粥——你心里一紧,穿着拖鞋就往门外冲。
一开门,门板就撞到什么人身上。你伸头一看,是房东太太。
她正提着小坤包在楼道里站着数钱,背上吃痛,转过头来狠狠瞪了你一眼,道:“你们商量好了是不是,我这合同里是要住满一年的,现在让我上哪里找房客去。”
“找房客?”
“不要装了,隔壁礼厢住嘛住嘛,连男朋友都住出来了,现在的年轻人……”房东太太撇撇嘴,牵着狗就下了楼。
想起了什么,她扭头又说:“你尽快,从后天起我可是要按酒店算钱的。”
你只觉得心里一空。房东太太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楼梯口,远远仍能听见小狗的叫声。马嘉祺的门没有锁,你迟疑了片刻,拧开把手迈了进去。
这个家你曾经来吃过一个月的饭,你曾在门口“咚咚”地敲门,求它的主人出来换一换灯泡;
你在没有开灯的夜晚与他共跳一支没有曲子的舞。而今这里仍然有着一张餐桌和两把椅子,卧房里仍然有床,被子掀开一角露出松软的白棉布床单,衣橱里还挂着他为数不多的几件黑色衣服。
毛巾晾在阳台上,你走过去一摸,湿湿的,仿佛主人才刚刚用过。
你闭上眼,热泪滚落下来,第一次知道眼泪原来真的是有温度的。
退房那天走得很顺利,你原也没什么行李,违约金马嘉祺走的时候替你一并交过了,你想,他不必如此的。但这话到嘴边又想起,他已经走了。
隔壁很快住进新的房客,是来北京打拼的小情侣。闹哄哄地搬家具、安窗帘,言笑晏晏,有细水长流的稳妥。
你拎着行李箱磕磕绊绊地下楼时,回头一看,这公寓不过是北京城里万万千千不起眼的栖身地之一。人走茶凉,下一任住客搬进来,又重新开始各人的悲欢喜乐。
无论前人有怎样的故事,都不会再有人记得。
你黯然地从兜里掏出手机,拨出一串号码,说:“我回来了。”
......
“缨嫚同志这次完成得很好嘛。”机场外,来人走上前拍了拍缨嫚的肩,顺手拿过行李塞进后备厢。女孩显见得有些倦,窝在车后座上一声不吭。
“怎么了,平时叽叽喳喳的,今天打蔫了?”
“王队,接下来还有什么任务?”
“好好休息就是你的任务。你可真行啊,马嘉祺反侦察能力一流,好几次都被他溜了。你这回可立了大功。话说,你是怎么知道他要潜逃的?”
“他会做饭,饭菜有一个人抹不掉的印记。”
“哦?”
你张张嘴,想说点什么,最终把话咽了下去,心底莫名生起一份私心:那碗清清淡淡的白粥,是你和他之间干净温热,无法被诉诸于口的所在。
一个人只有在所爱面前才会毫无保留地暴露,而你正是利用了这暴露。
回到局里,缨嫚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表彰,作为队里年纪最小的女警,你在短短十个月的卧底中掌握了大量马嘉祺的一手资料和犯罪证据。
周末,局长到余家吃饭,推杯换盏之间毫不掩饰对缨嫚的喜爱。
他说:“老战友,我跟你比了一辈子都没输过,谁想到了小辈,你们缨嫚把我儿子彻底给比下去了。”
老余很得意地笑,又唤缨嫚:“来,给你伯伯倒酒。”
廉江地处广东边陲,夏天日光倾城,一天一地的金色扑下来,空气里常年游荡着海风腥热的气息。
缨嫚下班开车回家,等红绿灯时一恍惚,会想起从前当余婉的日子。
亲近的北京话,甜糯的小吃,总是下着雨的阴凉天气,像是就要拿着锁匙开门,一转头,高大清瘦的马嘉祺倚门站着,两只手插在裤兜里,嘴角斜斜地一笑,唤你“余婉”。
“哎。”
你应,一激灵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踩了油门,横街驶过来的大众拦腰撞上来。
在失去知觉前,你心里竟然平静得没有一点波澜。你想自己也许就要死了,原本下半身的麻木渐渐蔓延至全身。
然而你竟不怕,毕竟作为余婉的身份,你早已消失过一次了。
......
病房里向来不容易睡好,但局里给缨嫚特别安排了单人房。位置在走廊的尽头,清静不被打扰。
窗外种着绿意茵茵的小叶榄,爸不许妈来,只说你又出差了,自己一天三次过医院送饭。
你现在腿上裹着重重的石膏,手术麻药过去后是钻心的疼痛,但你从来没有哼过。
老余叹了口气,心想:女儿果然长大,再不是从前天真娇憨的模样。
老实说,刑侦队要让你去北京时,他心里没有一刻不担心。谁想到出任务平平安安,反而回到小城,差点在车祸里丧命。
局里对这次车祸非常重视,多方严密调查,证实了不是来自犯罪团伙的打击报复。
心理医生从病房看过后出来,只说你出事是因为精神压力很大,需要静养休息。
所有人都以为你是北京一案做得伤了神,便没有人轻易来这病房打扰你。
日子漫长,海滨小城的夏天是日光里镀过的金针,一寸一寸扎得人寂寞难忍。
你细白的脖子在枕头上扭来扭去,只觉得躺得腻烦。央父亲带了几本书来,老余却怕看书伤神,只说自己不会挑,暗地里拣了本你幼时读过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带来。
那本唐诗每页只得一首,注着拼音,背面画着插图,是小孩子字也识不全的简明版。你心里发笑,后来就拿着这本唐诗打发长日。
你住得心里发慌,想要回家,老余说怕妈妈看到会哭,哄得你一时安静下来。
但住院这么久,队里的同事一个也不来看望,你吃饭时直跟老余抱怨他们没良心。
“大家都忙,哪里有工夫来。”老余给女儿喂饭,陶瓷匙子小心翼翼递过来,像你又变成了三岁的幼童,“你还记不记得,小时候我出任务一走大半年,进门胡子拉碴的,你管我叫叔叔。”
你笑,你当然记得。父亲一直说,做刑警就是要有牺牲自己和所爱人幸福的觉悟。
黄昏时,窗外的天色渐渐积郁起来,疾速翻滚着的黑云从遥远的海面迫向这座小城。
护士过来换药,顺便拿了老余留在床头柜上的晚饭盒,放到微波炉里帮你热一热。
今夜天气预报有雷暴和大风雨,老余腿上有旧伤,中午就讲好不过来了。
雨下下来的时候你正躺在床上背诗,闭着眼也听得到窗外轰然的雷鸣。
雨水瀑布一样倾泻下来,小叶榄的树枝“啪啪”地扫着玻璃,有种末世的倾覆之感。
窗玻璃不知什么时候被吹开了,天蓝色窗帘被风吹得鼓胀如帆,冷风穿梭直入。你职业性的警觉上来,睁开眼,室内空无一人。
你扭过头不去看那窗户,过了一会儿,风渐渐消失了。你努力克制自己,在静谧里,你几乎能听见他衣服上的雨水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。
......
马嘉祺在赶过来的路上时,一直想着那双眼睛。他活了一世,见过那么多男人和女人,可没有一双眼睛像你。
纯然明定,总让马嘉祺想起静美的雪天。
有一年马嘉祺在东北,目睹仙鹤从温泉中起飞,雪地里孑然一身,有种落落寡欢的美。
那次他死里逃生,后来辗转过许多地方。到了北京,他又一次在一个人的眼睛里看到那时的景致。
后来他在西北的隐秘据点被警方连根拔起,幸亏他性格一向多疑,临时换了落脚点,赶回北京,知道有人泄露了自己的货量和行踪,但没有人可以这么贴近他,除了这只白鸟。
“好久不见。”马嘉祺搬了把椅子坐在你的病床前。
你定定地看着马嘉祺,他注意到你眼里有戒备,只淡淡地说:“你不要怕。”说完低头将病床摇高。
做完这些,马嘉祺才从雨衣里拿出一个精钢保温壶,没有碗,就将就着用你喝水的马克杯。
香糯的骨肉粥从保温壶里汩汩而出,你注意到马嘉祺的手,新伤加旧伤,累累如老树的枝干。
他的头发显见地长了,乱糟糟的。黑胶雨衣穿了许久,棉T恤领口散发出酸馊的气味,是很久没有安生过日子的模样。
丧家之犬——你脑海里忽然蹦出这个词。
如果你没有记错的话,马嘉祺应该已于四月二号凌晨在北京附近的小县城落网。
其后你返回了小城,再后来出了车祸。关于他的案子,你再不知道分毫。
窗外雷声轰隆,风雨大作,两个人默然相望。
明明有那么多问题要问,那么多话要说,可此身此境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马嘉祺起身绕到床尾,看了看你的名牌。
“余婉啊。”马嘉祺弹一弹那卡片,嗓音疲倦而嘶哑。
你默然低头。
马嘉祺叹了口气,又绕回到床前。递粥的时候他不小心碰到你的手,你立即缩了回去。
在缩回去的那一瞬你就后悔了,小心翼翼地抬眼看马嘉祺。
可男人的脸仍然是淡然的,没有一丝波澜的样子。你心里知道,他一定被伤害了。
你只喝了两口,说吃不下了。马嘉祺起身接你的杯子时,很自然地取了一张纸巾隔在手上伸了过来。
“我要走了,这次来是给你……”马嘉祺从雨衣内袋里掏出一个黑塑胶袋包裹好的东西。
你仰起脸看他,恍惚间像回到了你们初相遇时,他站在老式木凳上说“好了”,你扭头摁开关,鹅黄色灯光将室内笼在一片温柔里——
你忽然看见马嘉祺笑了,尽管他眉心红如地狱的沸点。你捂住耳朵,却仍然听得见子弹从骨肉中穿破时沉闷的撕裂声。
......
队里没猜错,逃犯马嘉祺最可能出现的地方,是你的病房。
狙击手从对面楼撤走,马嘉祺的尸体也被警方以最快的速度从病房里清理出去。
王队进来时望见你正在喝粥,头埋在马克杯里。走近了他才发觉,你的肩在微微地颤动。
“小余啊,抱歉。”
这么说来,从给你安排病房开始,就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局。你点点头,表示理解,却仍然不肯将脸从马克杯里抬起来。
从前父亲只告诉她,做刑警要有牺牲自己和所爱之人幸福的觉悟,却没有告诉你,一个警察爱上罪犯该如何觉悟。
王队将黑塑料袋包裹着的东西交给你,说大雨里狙击手在对面楼看不真切,以为马嘉祺要掏枪报复你,所以才急忙开了枪。
但这也没什么差别,马嘉祺罪大恶极,即使判下来也是死刑。
你没有问队友们到底埋伏了多久,也没有问为什么不告诉你这次行动。
王队走后,你打开那个已经被揭开检查过的塑胶袋,这才看到里面是一只摔碎的树脂小猪。
白色背心套在胖胖的肚皮上,蹄子上那颗金色的星星和小猪的脸一起碎得不成样子。
你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
其后的许许多多个夜晚,你没有梦到过马嘉祺。你如常地工作,执行任务。人生如此沉重,很多事情原不必说出口。
只有一次你路过北京。那是十年后的春节,你难得休假,陪父母去北京旅游。
凌晨,你悄悄从宾馆出来,打车去了两小时路程外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
站在天微微亮的个园里,白雪覆盖在竹叶上,清白静美,像从没有见识过天地间的任何污垢。
你说:约好的,我来了。
你从兜里掏出一副黑色手套,这手套是十年前你从北京某个故人的空房间里拾到的。
你将手套埋在个园里,雪越下越大,分不清是雪片还是眼泪。
又或者是你在黎明未醒的梦中,一抬头看到马嘉祺就在雪中站立着,一张年轻的脸,像刚刚去TVB试戏时的梁朝伟,脸上有种男孩气的散漫和快乐。
马嘉祺向你伸出手,这一次你没有退缩。
隔着永恒的空气,你像搭着某个人的肩,像某个人也拥你在怀里。在清晨万籁俱静的雪地里,彼此无声地舞着。
我在夜里跳舞
在夜里跳舞
用我支离破碎换你一刻的眷顾
不归的归途
不落的夜幕
统统陷入一场大梦之中再虚度
在夜里跳舞
我在夜里跳舞
留给这个城市不值一提的风度
不要人在乎
不要人羡慕
若我能与你同舞
......
End.
_
啊啊啊啊是五一没人看吗~
喜欢就点个赞吧~
最后祝小炸们演出顺利!